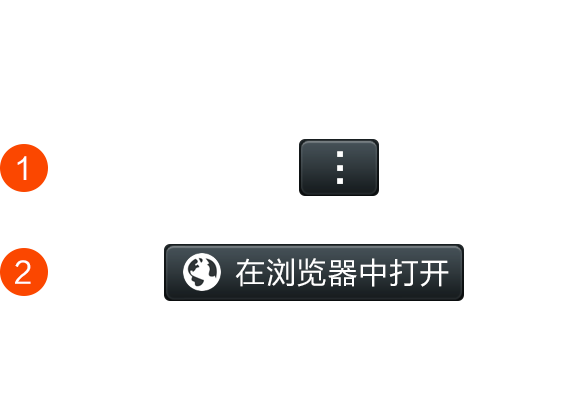稿件详细
抚摸我脸颊的那双手
那天,我倚在客厅的沙发上剪指甲,母亲走过来,把她的手伸给我:“顺便帮我把这个指头的指甲剪剪,我眼睛不太好,看不清楚。 ”很惭愧,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为母亲修剪指甲。
其实,母亲的手指甲很圆润,我想,年轻的时候,一定也如人们常常形容的那样修长如葱吧。可是,如今已经被刻上了岁月的斑驳。母亲的左手的中指第一节是弯曲的,几乎有g0°
上面布满了疤痕。这个指头是母亲在割草的时候多次用刀伤到它,后来,据说是里面的筋被割断了,就直不起来了。这样弯曲的手指在后来做饭切菜时,又多次切伤,就成了现在这副伤痕累累的样子。
母亲的手放在我的手心,除了能感觉阵阵的温暖从她的手心传到我的手心,其他的感觉就像握着一片粗糙的树皮一样。
我将指用刀放在母亲的拇指甲上,这个指甲已经变得又厚又硬了,我用力捏住指甲刀,使了很大劲,那指甲才“咔”地跳走了一小块。母亲笑了,这手掌的皮厚,连指甲也这么厚了。好熟悉的话语啊!小时候,我常常长冻疮,整个脚肿得红红的。母亲干完活儿,总会带回一些麦苗叶子,或者在邻家找个药柑回来,将这些东西在锅里煮沸,然后就抓起麦苗的叶子或者柑橘皮敷在我的冻疮上。我的脚都觉得好烫好烫,可母亲的手,就像没感觉。她说:“我的手不怕烫!”

 鲁公网安备 37092102000160号
鲁公网安备 37092102000160号